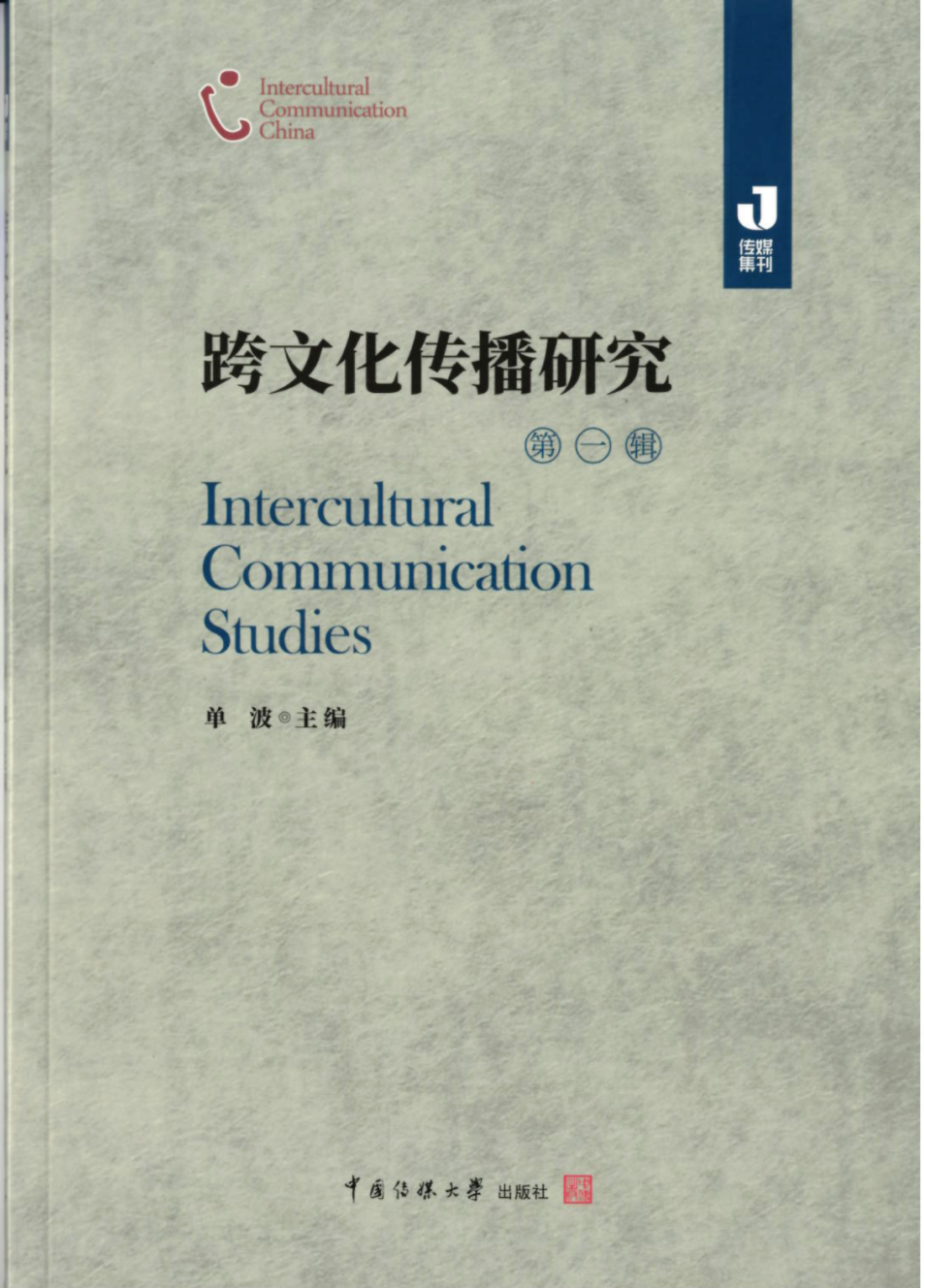《跨文化传播研究》| 序言与寄语
发布时间:2020-09-02 15:37:28 点击数:
近日,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和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出版的学术辑刊《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一辑)正式面世。《跨文化传播研究》立足人类自由交往的需要与实践,希望通过经验研究揭示把各种跨文化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提供保持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可沟通性的独特路径,通过批判研究揭示文化间的权力关系,重构人类的普遍交往;通过学术对话展现特定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探索,及其与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增进各文化区域的学者对跨文化理性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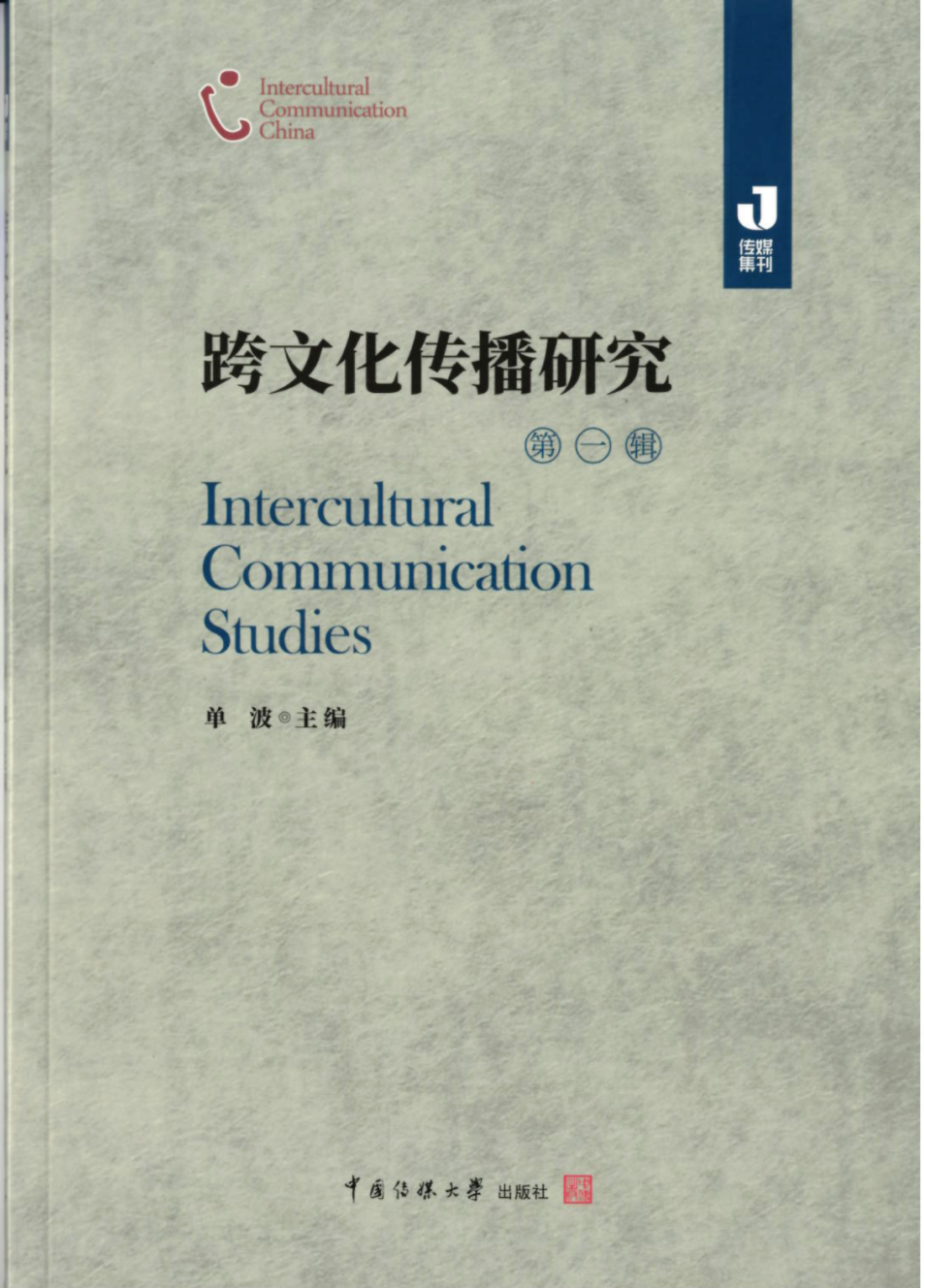
序
当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ICIC)进入第十届的时候,《跨文化传播研究》辑刊面世了。自2003年以来,这个会议聚集五大洲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基于东西方跨文化经验的对话,重建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域,形成以“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为中心的多维问题意识。虽然“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讨论充满不确定性,但这种讨论带来了一种可能:共创一本定期出版物,建构多元文化对话的跨文化传播学术空间。
跨文化传播来源于全球化,又接受着全球化的挑战。当人们怀着乡愁加入全球流动,走进大都市的陌生人社会,遭遇没有保障的跨文化交流,尝尽群体间偏见、歧视与污名化,落入与他者交流的困境,“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就成为每一个人的追问。陷入困惑的人失去交流的力量,而清醒的人则努力用交流治疗交流的病痛。当人们适应了全球流动,说着英语,哼着流行歌曲,秀着品牌,浏览着大数据,欣赏着时尚表演,全球化又成了跨文化传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蕴含着暴力,使一切都落入权力支配体系,把人引向同质化、文化霸权、文化割据的世界。全球化把人们推向跨文化传播之路,但人们回头一望,这条路又被全球化毁坏了。
然而,人的自由天性使人不甘于忍受全球流动的苦痛和全球化的暴力,而是把全球化制造的跨文化传播难题变成一个通向交流反思和实践的公共论域,试图重构普遍交往,使其通向主体间性传播和文化间性传播。令人沮丧的是,全球化的“中心-边缘”范式分割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移民流动的“北方”目的地成为跨文化传播理论话语中心,而“南方”成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旅行之地,这使得跨文化传播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由“北方”所界定的主题,诸如身份、文化适应、传播动态性、跨文化能力、群体间偏见、刻板印角、文化差异、跨文化教育与培训等。不可否认,身处全球主流社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大多具有亲边缘人的“情感结构”,但由于全球化消解了非中心的多元文化对话者的显性存在,其理论思维依然是不完整的。这些依赖单一理论的思考者难以迂回到多元文化的跨文化智慧之中,因而难以形成类似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那样的“思想的震颤”,“体验思想在异城漂流的感觉,以致找不到共同的范围和框架,无法归类”。失去“思想的震颤”,跨文化传播研究常常呈现某种理论重复状态。而“南方”的学者又很难摆脱知识生产的权力支配体系,无法有效构建可交流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空间。
“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像一头大象。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语境的人都能触摸到问题的特定“部位”,相互见证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相互提供文化智慧、提醒理论盲点,像古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家分享“盲人摸象”(典出《大般涅檠经》)的智慧一样,保持文化间的心灵对话,拓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维空间。
我们希望《跨文化传播研究》真正成为多元文化对话的跨文化传播学术空间,深深扎根于人类自由交往的需要与实践,通过经验研究揭示把各种跨文化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提供保持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可沟通性的独特路径;通过批判研究揭示文化间的权力关系,重构人类的普遍交往;通过学术对话展现特定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探索,及其与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增进各文化区域的学者对跨文化理性的理解。
我们深深寄望于跨文化的交往理性,希冀以走向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表达的姿态,推进跨文化传播研究和理论对话,以见证那隐含在多元文化实践中的共享的理性。
延斯·奥尔伍德 Jens Allwood
(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
我们需要跨文化传播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在这个时代。
有人会认为,我们已经对跨文化传播有了足够的了解,因此不需要更多的学术研究。我们已经对跨文化传播有一些了解,即便这样的说法成立,如果负责国际事务和种族间关系的决策者更加了解跨文化传播,则更有益。再者,我们肯定不是对于跨文化传播无所不知。在许多领域,我们的理解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所以,是的,我们应该对跨文化传播进行更多的学术研究,即使不是每个科研资助都意识到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研究。
目前,跨文化传播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所有国际联系和种族间接触的特点。例如,在国际政治、军事联盟或对抗、商业、医疗、科学、旅游、研究等领域都涉及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合作、冲突或竞争。
然而,之所以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跨文化传播,一方面因为它是这个星球上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本身就很有趣,另一个原因是需要它来为国家和种族群体之间的成功联系提供更好的条件。
学术研究可以维持和改善我们已经理解的事物,但同时也要接受批评、怀疑和新的思想,而不是寻求一些快速的、看似有用的解决方案和培训计划,这些有时会助长偏见和恐惧,是弊大于利的。我们不想出于商业或政治原因来重复研究我们已经知道的事物。例如,我们需要更好的论证来阐述文化模式和文化变革;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文化如何影响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因素如何与信念、价值观等其他文化因素相互作用。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我们应该囊括社会科学家、人文和语言专家、通信和计算机科学专家等,实现更多跨学科的合作和多元方法的融合。
早在语言出现之前,人类就已经通过遗传信息在群体间的交流取长补短,从中受益。人文与自然相互印照,相辅相成,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由此产生。21世纪地球村的概念更加凸显。多元文化并存、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成为一个普及性、常态化的概念。新冠疫情更加警示我们,人类需要形成一个交流畅通的命运共同体来应对未知的紧急事件。大数据的数据挖掘技术,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特征,对我们认识世界并获取最优化的交流方式有着非常好的借鉴和启示。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非常直白地告知人类:在这个地球上,人与人、人与物都是相关联的,技术让群体之间无法分割。跨文化互动行为成为必然。文化与文化间通过理性对话调解矛盾,消除冲突,相互影响并改变彼此。至此,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实质和内容袒露无疑。有人类的存在,就有文化间的交流与交融。
信息全球流动、共享的时代,也必然是多元文化跨时空流动、运行的时代,面对空前错综复杂的世界环境与全新格局,我们需要树立与之相协调的全球多元文化观,需要建立与科技文明相适应的跨文化传播观及实施高水平的跨文化沟通实践,超越急功近利的政治经济观,全面化解危机,融入世界,占据主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族对象进入共同体,其文化与他者文化沟通、碰撞会日渐频繁,同时可能会成为新的潜在合作伙伴。即使在共同生存的意义上,理解的迫切性也日益凸显。尊重、理解、共情、包容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是实现人类大同的先决原则。
因而,今天的世界格外需要新型的跨文化传播的学术与相应的沟通实践。《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一辑的出版,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很好的践行。
陈国明 Guo-Ming Chen
(美国罗德岛大学教授)
跨文化传播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社会的重要性已不喻而明。广大深邃的全球化潮流与突飞猛进的新媒体科技的有机结合,已给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冲击。不论是跨国间的移民,病毒的扩散,文化的流动,或经济的活动等人类社会不同的面向,在范围的增广与速度的加快上,可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也说明了文化间个人与个人,组织与组织,群体与群体,以及国家与国家直接接触频率的大大增长下,彼此之间经由沟通来相互理解,或谈判协商以解决问题与冲突的重要性。这也正是经由彼此文化的理解,来达到沟通目的的跨文化传播学主要的任务与追求的目标。
因此,跨文化传播学不仅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显学,它对文化的理解与跨文化沟通技巧的实用传授,也是当今人类社会在学术与生活层面同时不可或缺与必需持续加强的学科。
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 Clifford G. Christians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教授)
在全球媒体技术正改变历史的分水岭时,老师们和学生们都需要具有全球性思维。我们的教学、课程和研究议程首先必须是国际性的,而不仅仅是最后一句话具有国际性,或是一个断章取义的结论。世界曾经属于少数上层社会,直到今天的数字革命,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地理位置的人们都可以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传播学的研究要恰当地以世界为中心,必须重视特定的人类生命价值,而不仅仅是普遍的人类生活。肤浅的跨国主义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典型文化中抽象出来,这无法正确研究这个世界。随着传播学的经验增长和概念成熟,需要新的轴心来取代单一文化轴心。当学术界以全球思维展开工作时,不应局限于东方和西方、北方和南方,抑或民族国家。当全球都朝着消费主义和数字化的方向发展时,本土声音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此,今天学术研究的中心挑战是文化身份认同及其各种特性——多元性、多样性、本土语言和多元文化社群。
于格·欧梯也 Hugues Hotier
(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教授)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目睹不同社会的人们相互接触的情境,揭示出可能导致误解甚至冲突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例如,与民族文化相关的物理距离方面,我们应该感谢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他用人类空间关系学(proxemics)所做的概念化,保留了对社会误解的纯粹观察。再如,运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互动仪式》等著述,可以展示并分析那些导致严重不相容的文化实践。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正是学术范式使我们能够归纳多元观察,揭示隐含意义,并最终帮助理解。
如今,任何人都可以自信地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任何内容,并大规模地传播未经证实的观点,从而助长了最严重的民粹主义刻板印象,尤其是在跨文化传播领域。而学术研究提供了两个保证:它是在有意义的理论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并且拥有方法论,保证严谨性和可靠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仅需要展开这种研究,而且需要发表和广泛传播。知识的进步显然是学术研究者的目标。但是,当我们谈到跨文化传播时,知识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目标,它也是为社会和组成社会的人而服务的。

温迪·利兹-赫维兹 Wendy Leeds-Hurwitz
(美国跨文化对话中心主任)
我认为简短的回答显然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新冠肺炎疫情时代,我们已经了解到世界有多小,一个国家的行动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有多大。正如美国医学会主席帕特里斯·哈里斯(Patrice Harris)所指出的:“这种病毒没有国界。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疫情。当然需要全球合作。”这句话在我的社交媒体订阅源中出现多次,总结了显而易见的反应。如果我们面临全球性挑战(就像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准备好全球应对措施。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科幻小说,假设外星人入侵,理所当然地认为地方或国家的争执会被立即搁置一边,以对抗共同的敌人。我们现在就面临入侵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共同的战斗中合作。我们对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了解越多,我们就越能更好地形成合作。因此,尽管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新冠疫情时代可能很困难,但它也是至关重要的。
大卫·马修 David Marshall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教授)
跨文化传播领域对于理解我们全球人类世界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分隔极其重要。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在目睹各种形式的传播,它们通过新的技术中介将不同的文化连接在一起,这些技术中介有利于个人分享看法、图像和情感。同时,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这种新的传播模式也会回流至机构、政府和企业,并被聚合为监控数据。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最佳路径,探寻如何在人类文化中更好地分享、理解和连接政府、机构、公司和个人、社群、文化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前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出现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性,我们究竟该分享什么?如何分享?跨文化传播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不安全感,并应用于改善全球以及特定跨文化关系。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更多的学术努力对于构建更美好的当今和未来世界至关重要。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美式全球化”的进程中得以成熟和普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烙印。它强调的文化的异质性,从实际效果来看,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和吸纳。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见之大疫情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其局限性更加凸显,亟需实现从“跨”到“转”的理论和范式转型。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全球化时代,异质性的“文化杂糅”和由“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the rest)主导的“第三文化”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的主流,以TikTok、韩国“防弹少年团“等为代表的“转文化传播”(trancultural communication)日渐成型。从“跨”到“转”也将是中国学界全面走进传播学研究主流的历史契机,由单波教授主编的这本期刊的问世将为此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

我们这个时代已进入地球村,但地球村依然被丛林包围。从地球村的视角看,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和国家因为网络技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被紧密连接成一个人类文明共同体,相互交流、理解与合作的可能性日益增加。从丛林的视角看,我们的地球村其实岌岌可危,大自然的种种挑战此起彼伏,如极端气候、沙漠化、大瘟疫,等等;更糟糕的是,除天灾之外,地球村的人们拉帮结派,随时有可能分裂为彼此仇恨和厮杀的丛林部落,导致人祸不断,如战争、金融危机、宗教冲突、种族冲突,等等。如果要避免人类文明退回到丛林时代,除了不断加强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我们还有其他更好的选项吗?
单波. 寻找跨文化传播的可能性[M]. 单波. 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一辑).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1-3